上世纪80年代初,薛暮桥的专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和张五常的散文集《卖橘子的话》是那个时代最畅销的经济学书籍,随后是90年代的顾准文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现了类似《货币战争》这样的畅销书,被读者嘲讽为“金融奇幻小说”。在过去的几年里,经济学畅销书的主要类型已经变成了普通写作。这也是对经济和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所熟悉的一类书。
普通经济学写作由接受过学科训练的学者完成。其写作风格不同于专著和论文,在选题和文字处理上更贴近读者。有的写某个知识领域的常识,有的用一般方法讨论某个经济问题。这样做的学者是在试图把复杂深奥的知识变得简单。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对话经济学家蓝小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兰小焕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学。
在这两年的书市上,可能没有任何一本经济学类的书比《呆在里面》更“火”了。在本书中,蓝小欢结合学术研究成果,向读者阐述了过去几十年地方政府是如何参与和推动经济发展的,让读者看到务实而非意识形态的经济政策行为才是经济成功的关键。根据出版方世纪文景和作者提供的资料,《在里面》首次印刷10000册。自去年8月出版以来,已印刷20次,实体书销量超过65万册,成为今年经济类图书的一匹黑马。去年年底,《在里面》还获得了“新京报年度总写作奖”。我们采访了作者蓝小欢,和他聊了聊《写作在里面》的契机和他对通识教育写作的看法。
本文摘自8月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5版专题《在偶然与必然之间: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畅销之路》。
“出圈”出乎意料。
新京报:写《置身事外》的原因是什么?我了解到这本书原本是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准备的。
蓝小欢:对,《呆在里面》是我上过的一门课的讲义。内容基于我对中国经济现实的观察。在复旦大学,是高年级学生的课程,在香港中文大学,是研究生的课程。当时很受学生欢迎。因为学生的水平很接近,所以课程的知识结构没有区别。上课的时候比较复杂,写书的时候把复杂的数据和技术去掉。疫情也是一个因素。2020年爆发后,我不得不长期待在家里,于是有了写这本书的想法。如果没有疫情,也许我不会写这本书。
新京报:《在里面》去年出版后,吸引了很多经济圈外读者的关注。在豆瓣网站保持了极高的读者评分,同时多次登上各大销售平台和实体书店的畅销榜。之前有没有想到会卖的这么好?
蓝小欢:一点也不。我在写作的时候,设想读者主要是学生,但现在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读这本书,比如从事招商引资的政府官员,金融专业人士,企业家等等。打开网站,大概有好几页关于这本书的视频,有的点击量甚至达到了上百万。同事开玩笑说这本书创造了一个产业链,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在里面》,蓝小欢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
新京报:地方政府和经济发展的话题对很多行业来说都很重要。很多人想从你的书中看到一些门道。你认为这本书讨论的主题是它畅销的部分原因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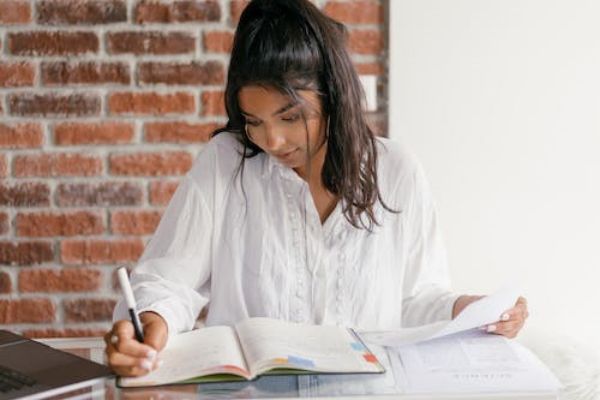
蓝小欢:从后诸葛的角度来说,这么说肯定是有道理的。任何接触过经济的人都知道政府很重要,但他可能不太明白政府为什么这么重要。有多重要?但我也想说,市面上有很多关于政府、经济、政策的书,不能说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什么空白。我书面的想法是,既然我们国家的企业和金融投资者都要和政府打交道,反过来政府在招商引资中也需要和这些人打交道,所以这本书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消除信息障碍,增进一些了解。对于在校学生来说,也可以从这本书里了解一些中国的经济情况。作为作者,不能有其他要求。这本书能实现这样的功能,我很满意。我刚给这本书起名字的时候,叫《中国政府与经济》,但是出版社告诉我必须改名字,因为没有人会买这样名字的书。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确定现在的书名。
新京报:你之前参与过当地政府的招商工作。这对你写这本书有什么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经历?
蓝小欢:参与地方政府招商的经历对我来说是根本。没有这些经历,就没有这本书。因为经历不仅仅是经历,它塑造了你对世界的看法。在此之前,我也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做过调研,从书本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知道这还不够。对此我深有体会,于是独自花了两三年时间参加实际工作,就是为了补齐自己的短板。所以这本书的很多内容都是我在实际工作中学到的。你会注意到书后面有参考资料,但我是先有想法,写下来,再用文献补充,其中一些也是当时教学的参考资料。但这些想法基本都来自于我在实际工作中的观察。
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事情,我们对事物的看法都是经历和沉淀的结果。我在参与招商引资的时候做了很多事情。比如我在谈判中发现,你甚至可以在半夜一两点钟约出地方官员。很多都是日常琐事,因为有了这些经历,你的观察自然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不会说任何一个单一事件就能完全改变我的态度或认知。我觉得没那么容易。这是要长期积累和沉淀的。用一个大词来说,就是跳出环境,然后反思。
这不是经济学家的专利。
新京报:《留在物》这本书和一般的学术写作在写作上有什么区别?你会有意识的区分这两种写法吗?
蓝小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涉及到如何把专业知识用大家都能理解的文字表达出来。这其中,有写作技巧,但尤其重要的是写作时的心态。有些人的写作是自说自话,他们只是专注于表达自己。但是我写文章的时候,很明确是写给别人看的,不是写给自己看的。无论是写论文还是写书,我脑子里总有一个谈话对象,不同的文章有不同的谈话对象。然后我会做很多改变。写一本书比写一篇论文更难,因为论文没有结构问题,但书很长,结构性很强。你需要考虑给你的谈话对象什么放在前面,什么放在后面。即使整本书通俗易懂,但内容顺序错位,读者也看不懂,所以肯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要花很多时间调整结构。我觉得和演讲一样,这里面有很多心态和技巧,有很多磨炼。
新京报:现在很多人会称你为“畅销书作家”。作为经济学家,你喜欢这个标签吗?有人会在经济学领域的书籍中区分“一般写作”和“学术写作”。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蓝小欢:这个很有意思。叫我“畅销书作家”比叫我“非畅销书作家”好吗?对我来说无所谓,标签有没有都无所谓。我要讨论的是所谓的“常识”。我写论文,我也写书,但我不能认同“最好的学者只写论文不写书”的说法。如果我们回头看看各个学科的经典著作,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或者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很难说它们是一般著作还是学术著作。在学科专业化的当代,学术写作和一般写作当然是有区别的。学术著作中显然有大量的优秀作品,比一般写作更强调观点的原创性,但两者并无根本冲突。
我从来没有把《置身事外》当成本科常识书。这是我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我用更多人能看懂的语言写,不代表不学术。现在很多人在看这本书,企业的人在看,博士生在看,本科生把它当成入门书,很多学者也在看。他们看的书难道不是学术书吗?书中任何一段都有论据支撑。为此我找了很多资料,有些不是最新的,但这本书的组织方式是新的。是我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只是用非正式的方式表达。

我也不喜欢用经济学中的“科普”这个词。它不同于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物学。对于后者,如果你不知道一些知识,那就真的不知道。你需要专家为你“科普”这些知识。但经济学不同。对于任何一个挣钱养家的成年人来说,经济学都是日常生活中不得不接触的东西。这不是经济学家的专利。经济学家不能“教”企业家如何经营企业,经济学家也不能把日常用品的成本“普及”给普通人。他们难道不比你懂吗?市面上有些书号称可以帮助读者赚更多的钱。我怀疑是否有这样的书。只能说经济学家看经济的信息不一样,看经济的角度可能更宏观更全面。经济学家可以与公众分享他们的观察结果,但这绝不能被称为“科普”。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用这种心态写书,没人会看。
对我来说,写作是因为我真的有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欲望,我也觉得值得一说。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和读者分享知识的状态。当然,有欲望也不一定能写出好书,其他外在因素可能是诱因。至少你表达出来之后,就不会太在意有没有人愿意谈论你在讨论的事情了。
采写/李永波
编辑/罗永波青
校对/薛静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