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最大的问题是违法成本低。

安徽的小雨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订婚照后,不仅没有得到祝福,反而遭到了网络暴力。这种“社交死亡”一度让她崩溃,甚至打乱了她的正常生活。
此前,杭州女子取快递时被谣言欺骗,女子因打赏遭网络暴力自杀,女生向学校捐5万元巧克力遭网络暴力,一名大学毕业生仅仅因为染了粉色头发就遭遇网络暴力...近年来,网络暴力造成的伤害或悲剧一再上演,如何控制网络暴力也是社会关注的话题。
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强调:“侵犯个人信息、煽动网络暴力侮辱诽谤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强调:“依法从严起诉网络诽谤、侮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侵犯公民权利的犯罪”。
订婚照被辟谣。
7月17日,订婚派对结束后,小雨在社交平台更新了自己的消息:“我们订婚了,以爱的名义,余生”。
本来是一个特别的纪念和分享,没想到变成了“社会死亡现场”。在评论区,先是熟人,后是粉丝的点赞和祝福。很快,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涌入,并伴随着“合肥某洗浴会所8号技师”的谣言。
当事人在公布订婚照片时被传。图片/截图
“其他地方的人可能不知道,但是合肥的人都知道8号”“这真的是8号,没人跟风”“网友这么厉害,一眼就认出8号?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看出来”。
一开始萧瑜并不在意,评论区回应谣言,但很快,这些评论的赞数就达到了数千。然后,越来越多的猜想出现了,很多陌生人甚至私信了她关于“八号技师”的细节,并对她的长相评头论足。
愤怒的小雨给评论最多的一位演讲者写了一封私信:要不要造谣求证?你的玩笑引起大家带节奏,原本开心的事现在变成了负面影响。请你删除它好吗?
一屏之后,网友的道歉显得轻飘飘的。在他的回答中,他只是开了个玩笑。
谣言传播的速度比小雨和未婚夫想象的要快。7月18日,小雨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并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声明。在声明中,她反复强调自己不是网上某俱乐部的8号技术人员。针对网友的人身攻击和辱骂,她已截图取证并报警。
在这份声明后,小雨还附上了社保缴纳记录、自己业务财务工作的相关证明、警方收到的案件回执。没想到恶评越来越多,这些证明再次成为攻击点。他们质疑萧瑜自证其罪只是做贼心虚。
“我第一次看到了互联网喷的力量...我澄清我不应该回应清朝。我不理,说不回应就是默认;我报警说我只是虚张声势。用诋毁找共鸣,用黑暗找狂欢。最后澄清一下,其他的交给法律,我就不删评论了。请不要取消您的帐户。”萧瑜在第二次陈述中控诉。
经历了几天的网络暴力,小雨的情绪开始不稳定。她整夜睡不着,吃不下饭,还时不时崩溃。即使她将社交平台设置为私密状态,也有网友通过私信质疑,甚至她的关注者和帮忙澄清的网友都遭到了人肉。
现在,小雨不得不请假处理这件事。警方受理此案后,小雨的未婚夫表示,他们正在收集证据,将对一些典型的造谣者进行起诉。
警方对该案的收据。当事人的图片/社交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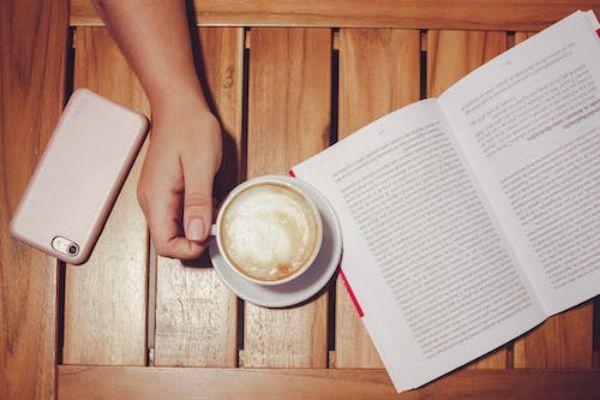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晶晶,曾代理过杭州一女子快递员诈骗案,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受害人报警后,公安机关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谣言发布者进行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
“但网络侵权与现实不同,很难发现谣言。”郑晶晶说,这个案件与杭州的造谣事件略有不同,杭州一名快递女孩在小区门口被两人杀害。警方在收集证据、确定发布者身份、到案等方面都有一定难度。应该是利用用户IP或者社交平台提供的信息来固定目标,而这些隐藏在网络背后的人可能来自世界各地,所以后续的处理还需要一段时间。
另外,从人格权的角度来看,造谣者严重侵害了受害人的名誉权,也可以向法院提起网络侵权诉讼,要求其删除所有侵权内容,向受害人赔礼道歉,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至于是否构成刑事诽谤罪,郑晶晶表示,相对来说,要看发布者的诽谤罪行为是否能达到严重犯罪的标准。《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侮辱诽谤罪是指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不过,郑晶晶建议,不管用什么样的网上造谣来维权,都要及时固定侵权的证据,以便后期追究法律责任。
导致“社会死亡”的网络暴力呢
近年来,网络暴力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关注。在小雨的经历之前,已经有过很多类似的案例。
今年4月,一名上海送货员帮助一名在家坐月子的女子给父亲送饭。由于该女子只给送货员200元食物,因此遭到网络暴力,最终坠楼身亡。同样,在上海,一个女孩给学校捐了5万块巧克力,学校被网络暴力攻击后崩溃。
2021年11月,一张女孩与爷爷的合影,被东莞飞辟谣为“少妻老头”。警方认为其行为造成了社会危害,严重违反了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经认真研究有关规定,决定以涉嫌寻衅滋事对吴某立案侦查。
在郑晶晶看来,网络暴力屡禁不止。最大的问题是违法成本低,但受害者维权成本高,维权时间长。“另一方面,网络暴力不是简单的违法问题,而是多重社会因素导致的综合问题。”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网络暴力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但根据行为的性质来定性。郑晶晶说,在民法实践中,通常会涉及名誉权、隐私权、网络侵权责任等纠纷,而刑事犯罪一般包括诽谤、侮辱、挑衅等。《治安管理处罚法》和《网络安全法》也有相关规定。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来规范网络暴力,也没有明确的法律内涵。
对此,她建议,应进一步明确网络暴力防治相关条款的标准,提高法律法规的灵活性和实用性,激活一些长期闲置的“沉睡条款”。随着社会的发展,经过充分的论证和研究,可以设立新的条例或者专门的立法来明确网络暴力的认定。
在今年两会期间,40名代表提交了一份联合议案,其中也建议对网络暴力进行专门立法。他们认为,目前国家虽有相关法律法规,但反网络暴力法律法规散见于诸多法律法规中,且法律法规不系统、不准确,反网络暴力法律法规存在滞后和疏漏问题。
因此,代表们建议,应对网络暴力采取专门的、系统的集中立法,制定专门的打击网络暴力的法律。同时,专门立法应对网络暴力的预防和惩治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明确网络暴力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治安处罚和刑事责任,加大对网络暴力的处罚力度,严惩恶性网络暴力事件,树立法律在网络环境中的威严。
此前,杭州女孩因送快递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第34批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陈国庆在评论中提到,此案的办理,对于在自诉案件已经立案但符合公诉条件的情况下,如何认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如何做好自诉程序与公诉程序的衔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郑晶晶看来,实践中,刑事自诉立案仍然困难,自诉到公诉的常态化衔接制度并不完善。依靠舆论推动案件进展,杭州案只能是个案效应,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网络暴力泛滥的问题。

“如果要追究网络欺凌者的刑事责任,一般需要受害人提起刑事自诉。但是很多时候很难达到立案的标准。即使受害者有充分的证据,还是有很多问题。”郑晶晶说,这类通过网络平台迅速发酵、危害性被放大的刑事自诉案件,普遍存在被害人举证难、立案难、维权难等问题。
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诽谤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发布。在这份解释中,虽然列举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案件,但郑晶晶认为,在当前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一规定仍然无法及时有力地促使办案机关对网络暴力案件启动公诉程序。
郑晶晶建议明确刑事自诉与公诉的衔接机制,进一步明确哪些类型的网络暴力案件可以作为公诉案件处理,或者制定更加完善、更符合互联网时代发展需求的实用标准。在今后严重的网络暴力案件中,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法律规定主动启动公诉程序,由公权力对违法者进行追究,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也有专家提到,要加强平台责任,制止网络暴力。今年4月25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启动了“清清白白应对网络暴力专项行动”,要求18个容易发生网络暴力、社会影响较大的网站采取建立健全监测识别、实时保护、干预处置、溯源、宣传曝光等措施,进行全链条治理,包括建立健全识别预警机制,建立健全网络暴力当事人实时保护机制,加大对违规账号、机构、网站的处罚力度。
作者:王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