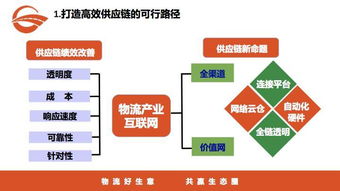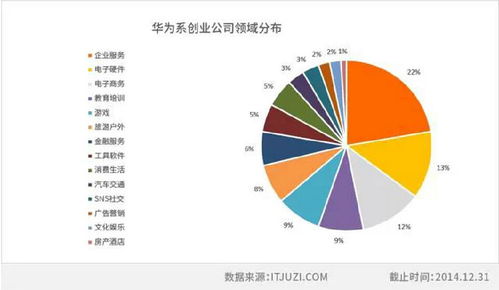文|刘丹茹
编辑|乔倩

来源| 36Kr Pro
封面|视觉中国
5月中旬,亿达资本创始合伙人杰西卡·王(Jessica Wong)在距离北京6596公里的沙特阿拉伯利雅得金融中心,一周之内接待了5家中国证券交易所公司的创始人。
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些过去在中国依靠内容、游戏和社交的公司市值下降了90%,以至于它们的账面现金远高于自己的市值。为了找到“第二条增长曲线”,这些创始人冒着回国被孤立的风险,去了中东。它与中东主权基金建立了合作,两年内在海上投资了16家公司,登陆沙特的13亿达资本成为这些创始人经常光顾的中转站。
“中概股在美国流了血,我们都在想:中国企业未来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在伦敦或者中东北非当地融资和撤资?”杰西娅告诉36Kr。
中东的兴奋不是今年才开始的。2021年12月,杰西卡刚刚从利雅得飞回上海。她一下飞机就收到了十几个出海项目的BP,最后有三个拿到了他们的投资意向书。
大量中国企业和投资涌入中东、东南亚、拉美甚至北非。一位出海的投资人告诉36Kr:“疫情很难走出国门。我们和创业者都在海外流通。美国、中东、东南亚、新加坡圈起来,然后迅速在各个地区设立总部。只要出来的人加倍积极。”
这种趋势的背后,是全球疫情以来,中国社交娱乐公司近两年的表现。
抖音被预测其收入将在2022年超过Twitter和Snap广告收入的总和;由于印度的禁令,欢聚时代失去了1.35亿个直播月,仅Bigo Live在2021年就赚了23.24亿美元。
昆仑万伟和赤子城,这两家几乎和工具出海时代一起没落的老牌公司,分别收购了k歌应用StarMaker和陌生人社交应用MICO,然后“逃命”,一年赚了20多亿人民币。
成为中东第一科技股的亚拉,直到上市才在国内接受媒体采访。当时创始人标着“YY之声+陌陌”,但两家都被欢聚时代低价卖掉了。后者股价三年下跌80%,而亚拉自2019年以来连续三年涨幅超过100%。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36Kr,“今年至少有两家社交出海公司准备上市。有的公司每个季度净利润都在1亿以上。国内有几个公司能保持这个水平?”
国内最大的社交公司陌陌,成立仅5年就找到了通过直播盈利的方式。社交产品后起之秀Soul在上市前提交了一份相当模糊的财报盈利模式。2019年和2020年分别亏损3.49亿元和6亿元,2021年一季度亏损4.09亿元。
热钱在创新的同时汹涌而来,但在许多大洋彼岸,除了大名鼎鼎的抖音,那些悄悄掘金,悄悄把产品传播到数百个国家的社会公司,都主动或被动地隐姓埋名。
我们好奇的是,他们是如何在海外生存并壮大自己的?
在中国生存,在中国赌博。
将时间线拉回到2016年,工具出海公司是第一个意识到未来至关重要的公司。
在昆仑万伟出海做工具和产品的那些年,造星人总经理夏凡团队在周会上投下大屏幕,显示着各个国家的获客成本。“美国是0.5美元,土耳其是0.2美元。在每个国家,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它涨了多少,我们能得到多少。”
在2014 -2017年之前,昆仑万伟工具类产品的净利润一年可以达到上亿。2015年,他们获得了脸书商业广告平台全球收入第一名。那一年,脸书在中国的全球会议有两个席位,一个给总裁张亚勤,另一个给昆仑万伟创始人周亚辉。
但很快,工具帆船赛道变得拥挤起来。
随着众多中国公司涌入印度,夏凡发现印度的获客成本和广告单价一度高于欧美国家,与印度用户的支付能力相当不合理。“市场陷入恶性竞争,很多同行疯狂铺广告、骗点击,工具出海的红利很快消失。”
同样以工具起家的赤子城CEO李平表示:“早期的手机操作系统和手机厂商都需要优化工具,但随着其生态系统的完善,对我们的业务不再有需求。”
脸书与谷歌的合作中止后,猎豹既失去了用户获取渠道,也失去了商业变现渠道,股价从巅峰时的50亿美元跌至不足5亿美元。
或者在转型中等死,几家出海公司选择了前者。
昆仑万伟董事长周亚辉是映客的投资者。他很早就意识到,单纯的直播流量还不够大,“直播+”可能是刚需。最后,他在“陌生社交+直播”、“短视频+直播”、“全民k歌+直播”中选择了竞争力较弱的一个,推出了全民k歌造星海外直播版。
当时在猎豹移动负责工具产品线的副总裁何燕丹,从2014年开始就想尝试短视频和直播。2015年,猎豹投资了短视频产品musically,于是她避开短视频,做了一个直播产品,直击用户价值最高的出海市场美国。2016年4月,Liveme在美国上线。
欢聚时代也加入了出海的战斗。Bigolive几乎与Liveme同时起步,前者专注于东南亚。
过去十年,工具出海,“出海”总有边际战场的意思。即使是下海赚了大钱的上市公司,由于产品远离国内用户,其影响力和市值也远低于国内互联网厂商。昆仑万伟创始人周亚辉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进入过互联网的主流圈子。”
何燕丹告诉36Kr,上一波工具下海的成功,是中国公司抓住了边际机会做本地化。“说白了,我们做了美国开发者看都不敢看的东西,把它做到了极致。”
但进入一个前景更加广阔的新战场,竞争瞬间进入白热化状态。
欢聚时代李学凌“孤注一掷”,不仅融资,还发行了10亿美元的债券。作为当时国内最懂直播的公司,他们不仅在海外做直播,还像2017年一样推出了短视频应用。
就在集合时间即将炫耀的时候,更疯狂的玩家入场了。抖音在中国上线才一年,字节跳动花时间让TikTok出道。
2017年,为了收购Musical.ly,张一鸣多次亲自拜访猎豹CEO傅盛。傅盛问张一鸣:“你看胜算如何?”张一鸣说,“我认为最多50%。”

十亿美元是50%的可能性。今天,当抖音的日常生活已经超过30亿美元,这当然是一笔好交易,但在当时,张一鸣的投资是一场豪赌。
张一鸣的英雄气概震惊了习惯于预算的海洋圈。“抖音每个月在谷歌上投资两三亿美元,当时我们都觉得太夸张了。”何燕丹说。
就连比Byte早一年出海的Aauto Quicker,最初也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发射策略。然而,在抖音在全球各大应用市场疯狂收购之后,Aauto Quicker的海外应用葵也不得不卷了起来。
Aauto quickent的离职中层告诉36Kr:“当Byte在海外突飞猛进的时候,Aauto quickent也在多位leader的带领下,在海外竞争不同的产品。非常相似的产品要在同一个应用市场竞争,投入的钱要花两次。一家代理公司可以更快地同时接到Aauto的两个订单。”
相比于Byte和Aauto Quicker这两个资金雄厚的短视频巨头,欢聚时代这个花了20亿美金,曾经是出海厂商的公司,现在只能称之为“中国工厂”。他们的策略是在用户增长和变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夏凡说,“一个大工厂每月花费1亿美元,但我们一年可能花费几千万美元。两者没有可比性。我们的使命是在扩大规模的同时赚钱。”
在张看来,这种策略是“心急”的。他在印度创办了一家社会企业,然后加入了字节跳动。对比Byte和其他厂商出海的策略,他说“如果微信处于用户快速增长期,考虑其商业化增长率也不合理?”
在用户增长和营收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社交出海公司最初在海外的日子并不好过。
虽然造星者是昆仑万伟孵化的“亲生儿子”,但总经理夏凡在2017年日常生活难以超过80万DAU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周亚辉的私人支持给员工发工资。
2016年之前,赤子城做了音乐、健身等不成功的尝试,在北美的校园社交、婚恋产品等方面做了各种尝试。就连MICO在2017年也每月损失100万美元。
欢聚时代做一个印度短视频产品的时候,至少有十几个类似的产品在里面试水。最后,月度数据最好看的是短视频平台Likee和通讯软件Imo,但这两个软件都不能带来多少收入。最有希望的Bigo,2019年亏损5.18亿,成为欢聚时代当时最大的包袱。
在不熟悉的海外地方,中国的直播平台往往被当成冤大头。某组织找几十个主播在各个平台骗底薪,同时挂四个手机直播,但是直播不好。
Bigo的一位海外经理告诉36Kr,“当时我们的预算很少,所以我们必须在街上找有标志的人,然后问人,我在这里有一个赚钱的生意。你会来吗?”
不死不活的局面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全球疫情爆发。
八十一难海上。
2020年是人类历史上永久标记的一年。大部分人的线下娱乐活动被终止,被迫上线。
据We Social和Hootsuite发布的《2021年10月全球数字化报告》显示,疫情发生一年后,全球社交媒体用户数量增加超过4亿。
Cmnet的新增流量早已枯竭,这些海外用户就像一片希望之地。
对公司成本一向极为敏感的夏凡发现,在疫情期间,他们的服务器成本在6个月内翻了3倍,这在财报中有所体现。2020年,StarMaker净利润增长超过3倍,至今下载量已超过2.4亿。
2019年刚在日本上线的k歌产品Pokekara的创始人胡,在负责今日头条和内涵段位的客户端产品。因为疫情,他们的产品被日本媒体杂志报道,被推荐为“适合家庭娱乐的物品”,迎来了一波用户增长,最终赶超本土产品,占据了日本k歌市场84%的份额。
Pokekara的日本员工告诉36Kr,虽然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意识到疫情是一个增长的机会,但与中国公司相比,当地公司和海外厂商在疫情期间举办活动或进行主题运营的反应速度要慢得多。
Jesscia举例说,美国产品出海,直接“空投资”世界各地相同版本的产品,输出标准的产品和服务。除了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其他国家很少派驻本土团队。而中国企业更愿意“坚守阵地”。
一家出海公司的创始人告诉36Kr,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大公司的海外负责人都选择回国,但是他们的海外员工认为别人都撤了,留下来就能抢占市场。
在技术层面,中国企业出海相当于降维。互联网泛娱乐负责人王琦告诉36Kr,在音频技术方面,之前有海外公司宣称可以在1秒内开始播放,但实际上延迟是2 ~ 3秒,达不到国内互联网社交产品实时通话400毫秒的水平。“以抖音为例,它比中国的TikTok落后几个版本,但海外用户已经觉得它非常有用。”
空之前的机遇让中国企业加大了海外布局,但是这种狂喜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他们迎来了“印度大撤退”。
崔怀洲是Aauto Quicker的第一任产品经理,也在欢聚时代担任海外短视频副总经理。在印度创业后,已经获得了国际知名投资机构的青睐,完成了早期投资流程。但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投资者立即撤回投资意向,并表示“其他原因可以讨论,没有政策风险的空间。”
损失最大的是之前押注印度的大厂们。
在印度被封杀后,抖音失去了2亿用户,但外界不知道的是,另一款类似印度“微博”的产品Helo也错过了一个巨大的崛起机会。在下架之前,Helo的日活已经有几千万,超越印度本土公司sharechat成为印度最大的社交媒体。一名前Helo员工表示:“如果没有下架事件,到今年年底,我们将拥有8000万至1亿用户。”
之前在印度的聚会时间,BIGO和likee在印度投资的几亿美元都花在了水漂。一位下海的印度企业家告诉36Kr,中国的科技公司把印度的互联网发展水平提升了一定的阶段,但最终没有一家中国公司成为赢家。
但印度带来的教训不止于此。
2019年在印度做短视频平台的崔怀洲算了一笔账。印度用户基数大,自然增长,投入少,可以把客户成本控制在0.001美元,但是带宽成本是中国的四倍,人均GDP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arup值是中国的五分之一。崔舟说,“要想在印度市场赚钱,至少比中国强20倍的商业模式才行得通。”
2020年后,大量社交应用退出印度。崔怀洲成为少数留在印度的企业家之一。他只是变得更低调了。他放弃了“先做用户规模再变现”的游戏,做了一个占星平台。他在网上招募印度占星师,让用户以视频付费的形式进行占星。2021年,他们的年收入达到了几百万美元。

在采访很多离岸公司的过程中,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用户根本不知道这是一家中国公司,我们看起来就像一家印度/日本/巴西/中东/美国的公司。”
在中东上市的亚拉,号称“中东小腾讯”,但总部在迪拜,注册地在开曼,RD团队在杭,在美国上市。虽然它的创始人和大股东都是中国人,但它在中国的曝光率远低于中东。
日本一家出海的公司在国内得到报道后,把文章翻译成日文发给了日本媒体。市场负责人几乎没等第二天就找人删除了“我们不希望日本用户建立这是一家中国公司的认知,这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总部设在利雅德的一家中东公司为了找到CMO,采访了至少50名中东当地人。最终的候选人不仅是一名沙特高官,还是当地最大运营商的市场负责人。
很多公司为了规避沉重的政治风险,选择当地人担任CEO,在新加坡、新德里等海外城市注册,服务器也放在海外。如果不被层层股权穿透,很难发现他们的主子是中国人。“虽然规模变大后可能藏不住了,但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先活下来。”
一家在海外同样能做到月流水百万美金的产品负责人,透露了另外一个出海公司们在国内选择低调的理由:“中国的出海圈很野蛮,一旦你的公司赚钱了,同行会以各种理由向苹果或者谷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