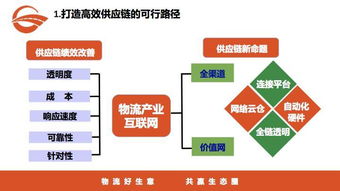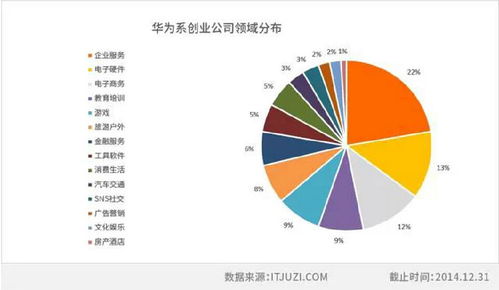“这是我二叔,曾经是村里的才子;这是我奶奶,一个天天蹦蹦跳跳的老太太。”这两天,一个名为“回村三天,二叔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哔哩哔哩视频走红。
有人在看完视频后回忆说,好像和我二叔一起走过了辛酸而充实的半辈子。

有人在问,我二叔真的存在吗?他现在怎么样了?会有直播吗?
视频的主人,也是二叔的侄子,名叫“一个猜想”,在7月26日晚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66岁的二叔和88岁的奶奶在老家村子里安安静静的生活,二叔不会直播。他也不想我叔叔和奶奶被打扰。
“视频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
“@一哥猜”曾经是10年的高中老师。不久前,他辞去了教师的工作,正在计划是否全职投身于视频制作。目前他的视频都是自己制作的,媳妇会帮忙。“文案自己写的。我媳妇买了个手机支架,我不会用。总的来说,镜头比较粗糙。”“@一哥猜”说视频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他删掉了一些比较传奇的细节,不想让人觉得意外。
二叔,姓赵
没想到火了。我和媳妇完全免流量,10-15万就玩了。我们只是想了一个愿望,也给自己定了一个涨粉的时间表。这次8点半才涨粉,早上就火了。太不可思议了。“回村三天,二叔治好我精神内耗”的爆款,是“@一哥猜”始料未及的。如果让他评价自己的风格,他说“没有风格”。“从画面上看,极差,画面不完整,因为是用手机拍的,有抖动。”
视频上线后,很多网友都很喜欢它的文案。"@ 丮丮丮丮丮"说几百篇文章把他和余华联系在一起:"我笑死了,不能侮辱名著。"
在这些评论中,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下年轻人的不同看法。“@一哥猜”觉得大部分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都是在城市长大的,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很长时间。除了旅游,他们还参观了农舍。我对农村生活没有感觉。但是,他们也在疯狂转发自己的朋友圈。“他们想的不是城市化,不是国家转型,而是把我二叔的经历投射到我高考复读、外貌焦虑、考研失败等事情上。”不管周围的人从它身上看到了什么,“@一个猜想”被很多人认真的回复所感动。他说当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会满脑子的想——我值得吗?!
“@一个猜想”说,他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出发点根本不在乎流量。一开始他给自己定的标签是“我二叔”,但在发布的最后一刻,他有点动摇了。“流量变得有些着急,标签也改成了现在的这个。”至于二叔能否治好“我的精神内耗”,@一哥猜”说:“二叔治不好我的精神内耗,我以后也会有精神内耗。最终,人还是要靠自己。我只是主动接近二叔,了解他,治愈自己。"
“我二叔”姓赵,但“@一哥猜”没有透露居住地。他说不希望任何人打扰我二叔和奶奶平静的生活。
认真的人不需要观众。
“一哥猜”给我二叔打电话,告诉他“热搜”、“哔哩哔哩”、“排行榜”,但是我二叔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尽管朋友圈疯狂转载,但在我家乡的村子里,除了我二叔,几乎没人知道这个视频。“村里80%是老人,10%是留守儿童,也不用微信。”
我的舅舅,我的外婆,整个山村的生活都没有改变。“一哥猜”他几乎没睡。大量的网友评论和私信,频繁的媒体采访,甚至电影改编邀请。他觉得我舅舅的故事不足以支撑一部90多分钟的影视作品,所以对它的热情不是很高。
越来越受到关注,甚至有人建议我二叔直播。“一哥猜”觉得应该表达一些态度,于是在微博上发布了我二叔不直播的回应。
“如果不是私信太多,回也不礼貌,我连微博都不想发。这个时代,没必要把事情挤得这么彻底干净。花都一个月没开了,留点东西也不好。每个人都平静地生活着。你一定要看到一个不快乐的结局才会快乐吗?我觉得这样特别不好。”
《伊戈尔猜想》说他不会趁热打铁,然后找个农村题材拍。他不想我叔叔的生活被打扰。拉面发生火灾后,拉面的乡镇挤满了红色的马路。吃了拉面的流量,鸡毛都剩一地了。
“我非常非常担心这一点。我觉得我叔叔对这种突然的曝光没有心理准备。我觉得这会让他不舒服。”《一个猜想》在采访的最后,带着恳求,“接下来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视频的人气,以最快的速度下降,然后不要让任何人透露我二叔住在哪个村,突然有人闯进我二叔家。”
就像视频里一个热评说的——认真生活的人不需要观众。
侠客岛点评:二叔过着我们向往的充实生活。
经过一番回忆,岛叔印象最深的画面是我二叔一瘸一拐前行的背影,而人们心中最震撼的,是他最朴素的坚韧与善良。他在斗争和困难中的自强不息和坚韧不拔令人钦佩。这不就是我们民族的素质吗?很多网友说治好了。就像up主说的“我有健康的肢体,上过大学,生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所以我值得过比二叔更充实的生活”。也许这就是作者认为自己的“精神内耗”已经治愈的原因。“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克服一切困难,争取胜利。”这是我二叔笔记本上的一句话。视频里还有一句话:“谁后悔没有?人们往往在临死的时候才发现。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他们一直在后悔过去。”让我们为二叔干杯,为明天干杯,勇敢地踏入人生的洪流,过充实的人生。“是的,这条人生之路最终一定会走向胜利。”
以下视频为文字版全文——
这是我二叔,曾经是村里的才子;这是我的祖母,一个每天跳蹦蹦舞的老太太。
他们住在这栋老房子里,它是在美国之前建造的。
我二叔小学第一,初中第一。全市统考从农村收了三张卷子,其中一张是我叔叔的。有一天,二叔发高烧回家。邻村的医生有一天在他屁股上打了四针,我二叔就残废了。
十几岁的舅舅躺在床上,再也不想回学校了。老师们三次上门劝说,我二叔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像个断腿的卧龙先生。
第一年,二叔不肯下床。他不知从哪里找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疯狂读了一年。
但是我舅舅的腿不是受伤,是残疾,久病不愈。
于是第二年,二叔扔掉手动,从床上爬下来,坐在天井里看天,像一只大青蛙。
第三年,二叔不看天了,看家里的木匠干活。木匠干了三天就走了。我二叔告诉我爷爷他看到了,让我爷爷去铁匠铺给自己做一个木匠的工具。三年来,二叔第一次走出大院,去生产队给人做板凳。他一天做两个,一个一毛钱,可以养活自己。
比如几年了,有一天我二叔像往常一样拄着拐杖来到生产队,队长跟我二叔说:“以后别来了,生产队没了。”
二叔问为什么,队长说:“改革开放。”
于是我二叔开始改革开放,在镇上的村子里四处游荡当木匠。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了当年的博士。他跟我二叔说:“要是今天,我早就被告上了,我这辈子都要承包你。”二叔笑着骂了他一句,又一瘸一拐地去上班了。
后来不知道是什么程序上的原因,舅舅的残疾证办不下来。他很失望,竟然拄着拐杖去了北京。他想去天安门广场的纪念馆,说要去看看他。
我二叔说改革开放很好,他也是。为什么?我二叔说:“他很公平。”
很快我二叔口袋里就不剩几个钱了。他的一个堂弟在北京当兵,我二叔考上了部队,是军人家庭。我没想到他做得很好。因为我二叔不喜欢搭讪人,只喜欢工作。他不知道从哪里借的木工工具。在那个部队条件还很艰苦的年代,他默默为战士们做了很多柜子和桌子。哪个士兵会不喜欢这个兄弟?
有一天,我舅舅的表弟去澡堂,看见一个老头和我舅舅坐在一起洗澡。我舅舅的表弟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那老头是他只见过几次面的头,正蹲在池子里给我舅舅搓背。
后来二叔回村,大家都问北京怎么样。二叔说:“北京人搓背很好。”
到了两个姐姐结婚的年纪,二叔很苦恼,他有自己的表情。所有的家具,每一张图纸,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玻璃,每一个装饰条,每一颗螺丝钉,我姑姑和我妈结婚时的每一幅画,都是我二叔一个人完成的。
你能想象当一个山村女孩在80年代结婚时,拥有这样一套家具是多么美妙吗?
奶奶家那么穷,姐姐嫁出去也有这么一套家具,婆家会高看一眼,说不定会对姐姐好一点。你可能会说我在吹牛,因为这是“上海牌”家具。但是你忘了这是我二叔。我二叔总有办法。他可以给你打上任何烙印。你想要什么牌子的?他还有天津牌,北京牌,香港牌,超豪华ok?
后来,小二叔收养了刚刚出生的宁宁。二叔在周围辛苦赚钱,大部分时间都在姑姑家寄养宁宁,很少陪伴她。

宁小时候经常被人在背后议论。一个被抛弃过两次的孩子,如何对这个世界有礼貌?
十年前,宁宁和男朋友结婚了。我二叔前期20万买县城房子,花了10多万。我无法想象他是如何保存的。
我二叔花了半辈子的积蓄给宁宁买了房子,却无比幸福。这是一个中国式的家长,一个可敬而可怜的中国式家长,卑微而伟大。
二叔三十出头的时候,迎来了做媒的高峰,但是二叔跟我说,他一直觉得这辈子只能照顾自己和别人,所以从来没想过。
我二叔撒谎了。当时隔壁村有个女人,有老公,有两个孩子。不知道什么样的机缘,两人的关系突然变得很熟,很快就熟得不能再熟了。她经常去我二叔家,我二叔也经常去看她,甚至在她老公在的时候。
两个孩子也很喜欢我二叔。后来,她作为我二叔家的正式成员,参加了家里所有的婚丧嫁娶,对我二叔很体贴,把他那乱七八糟的小屋收拾得井井有条。我二叔下班回来能吃一碗热饭,就顺手把今天结算的钱递给了她。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却没有离婚。我二叔的四个兄弟姐妹从一开始全力支持,转而怀疑这个女人只是我二叔的一点小钱,强烈反对。
还在上小学的宁宁,在班里管那个女的叫“老狐狸”,管女儿叫“小狐狸”。老实的二叔左右为难,不知所措。
后来,这个女人和她的丈夫死在城外的一个棚子里,他们是煤气中毒。我二叔一直没结婚。这段感情的细节我无法理解,嫂子也记不清了,但是二叔不愿意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既不是今天流行的神仙舞,也不是当年的救命。那个时候爱情来了吗?
几十年过去了,老朋友的故事也告一段落。到现在,除了一笔烂账,什么都没留下,烂在了二叔心里。出血,结痂,不能撕,一撕就把皮肉打垮。
就这样,又一个30年过去了,没什么可说的。是的,普通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普通人快进一万遍才能看。奶奶转眼八十八岁了。
现在农村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我二叔正是赚钱的好时机。他是真的想给自己多挣点养老钱,以后就不用拖累宁宁了。
但是奶奶现在生活不能自理,也不是很想活下去。有一次她甚至把绳子挂在门框上。中国人总说“生死”。为什么生与死之间还要再来一场“旧病”?
这不是上帝的不人道,而是怜悯。否则,我们每个人都会在70岁或80岁时死去,但我们仍然身体健康。我们会有多怀念这个世界?那不是更痛苦吗?从这个意义上说,“老病”是“生与死”之间的一次必要的锻炼。
所以前几年二叔出门,就开始把我奶奶放在车上。去别人家做木工,你把奶奶放在旁边的小板凳上。
这位66岁的老人带着他88岁的母亲。这个6688组合太酷了。
这几年,二叔不再做木工,全职照顾奶奶。早上给奶奶洗脸,晚上给奶奶洗脚,下午强迫她运动。
奶奶每走二十步就要坐下休息十秒,二叔每走二十步就要落后奶奶三米。赶上这三米只需要十秒钟,所以继续走。
这么默契的配合,上一次看到还是在乔丹和皮蓬身上。乔丹喜欢送皮蓬超跑,二叔喜欢给奶奶拉面,倒点西红柿炒鸡蛋。嗯,很好吃。
二叔从小对宁宁没什么教育,但今天宁宁成了村里最孝顺的孩子。可见,孩子以后孝顺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默默孝顺父母。孩子小,不瞎。
其实很难把我二叔定义为木匠。我在家的三天里,他给村民修了一个插线板,一个煤气灶,一个床头灯,一个玩具车,一个锄头,一个洗衣机,一个水龙头。
回来的路上,她被另一个阿姨拦住,修好了她家的门锁。进屋前,另一个老人给他家里打电话,说电磁炉坏了。舅舅去他家,发现忘了开插线板的电源。可怜的老人。回家后,我修理了一个祖母的旧机器和收音机。
奶奶有胃病,所以他给她针灸。人家觉得楼上门上光秃秃的木头不好看,就让我二叔自己设计,给别人刷漆。山顶建了一座庙,所有的龙都是我二叔雕的。
村里没有女巫,我二叔就当了算命先生。当然,亲笔是自己做的,竹筒是自己做的,笔记本是自己做的,卦是自己抄的。
他甚至有一天突发奇想,想做一把二胡。木须,铜丝作弦,竹作弓,鱼线作弓毛。我们这里没有蟒蛇,他就上山抓了些双斑锦做琴皮。你看,我叔叔总有办法。
我很想给你看看那把飘逸的二胡,可惜十几年前奶奶让我那笨弟弟拿二胡当锄头拉,就坏了。
这个村子里只有三样农具、家具、电器、车辆是我二叔不会修的:智能手机、汽车、电脑。因为我二叔没有这些东西。但是现在有个智能手机,是宁宁买的,拆几次就修好了。
夜深了。舅舅家的灯还亮着,那谁家的房子在修呢?
你听到锣声和鞭炮声了吗?村里没人结婚,但是年轻人都走了之后,野猪又回来吓唬野猪。
村子里只剩下几百个老太太了。如果东西坏了,就送到修理厂修理。先别说要花钱。如果是30里山路到镇上,如果坐车到县城,你下车他们连北都找不到。
舅舅总说能照顾好自己就好,其实是照顾全村人。村里的人都开玩笑地叫他歪子,但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爱这个歪子,离不开这个歪子。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二叔十八九岁。如果不是发烧后的四针,我二叔可能已经考上大学,成为一名工程师了。
单位的房子,国家的养老金,悠闲舒适,老有所养。邻村一位老人就是这种情况。他学习没有我二叔好。如果有,那该有多好。我的二叔一定会成为一个充满闲情逸致的老顽童——汪曾祺的父亲王力可·菊生。
看着眼前的二叔,总让我想起电影《棋王》里的台词:“他是个天才,只是生不逢时。他应该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名扬天下的。他不应该这么惨。”
真可惜。真的很可惜。
我问二叔有没有这样想过,他说没有。这种态度让我二叔成了村里第二幸福的人。第一个开心的人就是刚才我们村的“树先生”。
所以,你看,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不为别人负责的人,第二幸福的人是不回头的人。
谁不后悔?人们往往在临死的时候才发现。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他们一直在后悔过去。后悔是电影中主角崛起的前戏,是人生中让人沉沦的毒药。
我在华北漂泊了九年,有幸认识了几个人,但让我看到我们这个民族所有平凡、美好、强大的特征的,是我的二叔。

都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打好牌,而是打不好牌。舅舅这张烂牌打得真的很好,他在庄敬的挣扎和困难中的自强不息让我肃然起敬。
我四肢健全,我上了大学,我出生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我值得过比二叔更充实的生活。
时至今日,二叔依然在走自己的人生路。这条漫长的路最终会走向何方?
我叔叔床下有一本几十年前的笔记本。在笔记本的第一页,他摘录了一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克服一切困难,争取胜利。
是的,这条人生之路最终一定会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