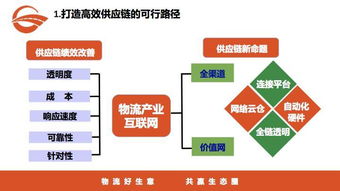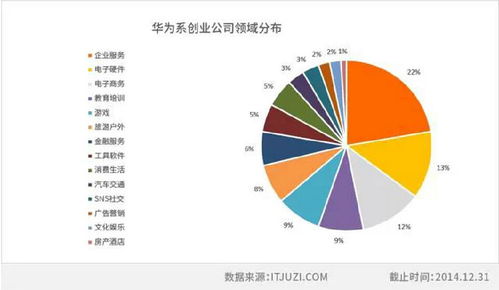近日,余华大片《兄弟》新版上市。余华和余两位“老朋友”进行了一场真诚而有趣的现场对话,谈兄弟、谈文学、谈人生。当晚直播间人气极高,观众超2000万。许多围观者表示惊讶和顽皮:“我终于看到活着的余华了!”
《兄弟》是余华的第四部小说,是作家继《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之后,在其巅峰时期完成的一部突破性作品。在余华的所有作品中,《兄弟》篇幅最长,语言最大胆,最能表达作家的创作抱负。小说讲述了李光头和宋钢两兄弟的人生故事,时间跨度长达40年。它不仅描绘了时代变迁中道德颠覆和浮躁放纵的腐败,也描绘了腐败中人性的活力、温暖和爱的伟大。是一部深刻易读的平民史诗。余华在采访中多次表示,《兄弟》是他最喜欢的作品。

在这场关于兄弟的对话中,余华和余带着读者再次领略了这部作品的独特魅力。
花了五个早上重读,又笑又哭。
首先,余表达了对余华作品的喜爱:“余华老师的《活着》出版的时候,我是第一个读者。《活着读书》他出版的每一本书我都读过。”在余看来,余华是一个特别搞笑的人,“写这么惨的书折磨读者,他却这么乐在其中,享受人生”。
至于《兄弟》这本书,余华这次把她的快乐和悲伤留给了自己。收到新版《兄弟》后,余华花了5个上午重读这本书。“从凌晨一点读到五六点左右,开始睡觉。一直笑,一直哭,一直笑,一直哭,看完。”余说他看《兄弟》的时候笑的比哭的多,因为他觉得余华的描写太搞笑了,但是看到人物最后的命运他会哭。“如果一部小说完全重而无美,那肯定是不对的。如果都是没有重量的美好,就无法深入到人性最根本的部分。”
在中国小说史上,《兄弟》是一部可以屹立不倒的书。
余华曾在《兄弟》后记中写道:“《兄弟》这本书是两个时代相遇后诞生的小说,而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两个兄弟。他们的生命在裂变中分裂,他们的喜怒哀乐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就像这两个时代一样颠倒。”对此,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只要人物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变迁,就是好小说,但前提是人物和故事本身足够吸引人。《兄弟》是一部通过生动的人物和故事反映时代的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我觉得《兄弟》应该是一本可以站进去的书。”
事实上,《兄弟》不仅在国内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在海外也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小说在海外出版后,《纽约时报》旗下的《时代周刊》、《世界报》、《法兰克福评论》等媒体纷纷发表报道,称赞这本书是拉伯雷、左拉、狄更斯等文学巨匠写的一部伟大的小说。此外,小说获得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入选法国《世界报》“二战后100部最佳小说”、瑞士《泰晤士报》“新世纪全球最佳作品”等重量级书单,无疑成为余华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品。
作家只是为了自己内心的需要而写作。
虽然《兄弟》在海外备受关注,但国内读者最熟悉的余华作品还是《活着》。余华接受了国内外读者的审美差异。此外,他还提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出版时,也被质疑“一个先锋作家怎么会突然写出这样的小说”。对此,余华表示,自己的写作不会被“体裁”和“标签”所束缚。“没有一个作家会为了一个流派而写作,作家只会为了自己内心的需要而写作。”
在余华看来,文学不应该仅仅被标签所限制,更应该被局限在文学本身的范畴之内。他提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关于《兄弟》的评论,这句话来自一位法国经济学家丹尼尔·科恩:“这是一本让你重拾对小说信任的书。我的意思是,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哲学的传承,因为它能让你了解人类的灵魂;也是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传承,因为它也能引导你理解社会的机制,以及人类的激情是如何被社会捕获、利用并由此塑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兄弟》具有超越文学的价值。“文学其实是包罗万象的。”余华说。
余华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仍然认为写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调整了日常作息,把写作时间从午夜改为每天下午。“我下午开始写作。晚上,我看书,看电影,然后睡觉。”另外,“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一开始要保持一种好奇心,他应该什么都想知道,因为如果没有好奇心,写作可能就完了。”
我们应该努力记住快乐的事情,忘记悲伤的事情。
在活动的最后,余再次表达了对余华作品的喜爱。“在一声声含泪的叹息中,我们可以知道余华笔下的时代,知道时代中人物的命运,也可以反思到我们自己身上。”他还提到,在作品之外,虽然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是要流泪的,但“我们仍然要失去我们的快乐和信心。”而余华则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快乐的时光远比悲伤的时光多,因为快乐容易被遗忘,悲伤记住的时间更长。"我们应该努力记住快乐的事情,忘记悲伤的事情."
虽然《兄弟》中描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余华说自己经历过的两次都“弥足珍贵”,“因为这种经历是从未有过的,反差之大令人难以置信。”正是那段经历造就了兄弟。余洪敏调侃道,“那个时代造就了你。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短视频,就不可能消耗自己的时间,看小说成了重要的爱好。”谈及“短视频”的力量,余华也一次次“投降”:“我才知道短视频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一两个小时过去了。”当被问及短视频对小说创作是否有好处时,余华说,“还没发现。”
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短视频时代的人来说,幸运的是,有《兄弟》这样的作品在那个喧嚣的历史中向我们展示众生相,让我们在平淡的当下再次咀嚼过去的丰富与厚重。在小说中,我们体会到了人物命运与自己的共鸣,和他们一起哭,一起笑,哀叹命运的无常,在这无常中,体味到人生永恒的喜悦和永恒的悲伤。
图书介绍:
《兄弟》讲述了一对性格迥异、命运相反的兄弟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不仅展示了中国社会在过去40年中的剧烈变化,还展示了不同人对生活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所走的不同人生道路。《兄弟》展现了人类情感的全景——从庸俗、狂热、机会主义到爱和内心的伟大,几乎都包含在内。在这个小宇宙里,没有人是孤立的,没有隐私可言。求爱和羞耻、痛苦或死亡的故事都公开发生在街上,这使小说本身成为一个世界剧院。
作者介绍:
作家余华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
1960年4月出生,198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细雨中呼喊》、《第七天》、《文成》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他曾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弗文学奖、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奖、法国国际外国小说信使奖、意大利朱塞佩·阿塞尔比国际文学奖、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文学奖和意大利波特尔·拉图斯·格林扎纳文学奖。
第二章试读
李光头
李光头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被歧视。只要他奶奶背着他在屋外,就有人指指点点,也有人像看西洋镜一样看着李光头。他们的嘴里都吐出一些难听的话。他们说李光头就是那个偷看女人屁股掉进粪坑淹死的人...他们说的话往往是无头的,好像婴儿在厕所里偷看女人的屁股。他们说这个小顽童和他的父亲一模一样。他们每次说的时候都有意无意的省略“成长”二字,只说一模一样。让李光头的奶奶脸色变得又红又白,奶奶再也不愿意背着他出家门了。她只是偶尔把他抱到窗边,隔着玻璃让他晒一会儿太阳。当有人从窗口窥视时,她会迅速闪开。就这样,李广一次次失去了阳光。他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他的脸失去了婴儿的红润,他的脸颊失去了婴儿隆起的肉。此时,李兰正患偏头痛,牙齿一直在咝咝作响。自从丈夫屈辱的去世后,李兰再也没有抬头看过别人,再也没有喊过,剧烈的头痛只是让她的嘴巴不停的咝咝作响。有时她在睡梦中发出“哎哟哎哟”的呻吟。当她把儿子抱在怀里,看着他苍白的脸和瘦弱的胳膊,她会流泪。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有勇气在阳光明媚的时候背着儿子上街。
经过一年多的犹豫,李兰终于在一个月夜抱着李广的头悄悄来到了街上。她低头趴在儿子的脸上,沿着墙快步走着。只有在确定前后没有脚步声的时候,她才会放慢脚步,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明月空,沐浴着夜晚的凉风。她喜欢站在空空的摇摆桥上,凝视着月光下闪闪发光的河水,无尽的浪花荡漾而过。她抬头一看,河边的树安静得像月光下沉睡的树,伸向空的树梢被月光覆盖,发出河水般的涟漪。有会飞的萤火虫。它们在漆黑的夜里上蹿下跳,来回飞的时候,像唱歌一样上下波动。这时,李兰会右手抱着儿子,左手指着桥下的河,河边的树,天上的月亮,还有飞舞的萤火虫...告诉他的儿子:

“这叫河流,这叫叫树,这叫月亮,这叫萤火虫……”
然后她无限幸福地对自己说:“多么美妙的夜晚啊……”
从此,缺少阳光的李光头开始在夜晚沐浴月光。当别的孩子都熟睡的时候,这个小镇上到处都会出现夜行小神李光头。一天晚上,李兰抱着李广的头不知不觉走到了南门,广阔的田野在月光下伸展开来。李兰不禁轻轻叫了一声。在她熟悉了月光下的房屋和街道的神秘宁静之后,她突然发现广阔的田野在月光下有着神秘的壮丽。怀里的李光头也激动了,双手同时伸向天空般宽阔的田野空,嘴里发出老鼠般的吱吱声。
许多年以后,李光头成了我们刘镇的超级富豪,决定去泰空看看。他闭上眼睛,想象着自己高高在上的样子。当他俯视地球时,他童年的印象神奇地回来了。他想象中的大地壮丽景象,是他母亲第一次抱他出南门时看到的:田野在月光下无限延伸。
李光头从他的母亲那里学会了什么是街道,什么是房子,什么是天空,什么是空旷明亮的月光下的田野...李光头那时候还不到两岁,惊讶地昂着头看着这个光明而荒芜的世界。
宋刚
第二天早上,宋刚肩上挎着一个竹篮出去了。竹篮里放了一圈细铁丝和一把小剪刀,他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乡下的苗圃。他买下那些含苞待放的玉兰百合后,就坐在苗圃里花草中间的地板上,拿出小剪刀把玉兰百合的枝叶剪下来,用细铁丝小心翼翼地一对对穿上。然后他让它们整齐地躺在竹篮里,挎在竹篮上,高高兴兴地走上了乡间小路。
宋刚在阳光下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地平线。走了十多分钟,他觉得自己在冒汗。他担心太阳会使这些饱满的玉兰树枯萎。他走到路边的地里,蹲下来摘了一些南瓜叶,盖在玉兰树上。他还是不放心,就去附近的池塘弄了些水来洒在它们身上。然后他信心满满地向前走去。他不时低头看竹篮里的木兰花。他们藏在宽大的南瓜叶下。有几次,他轻轻地掀开南瓜叶,看着下面的玉兰。他微笑的表情似乎是在婴儿时期看着婴儿。宋刚觉得自己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他走在广阔田野中的一条小径上。经过一个池塘,他会把水洒在竹篮里的玉兰上。
宋刚走回刘振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他忘了吃午饭,站在街上,开始卖他的木兰花。他小心翼翼地在竹篮周围插上南瓜叶,这样这些玉兰树就躺在绿色的周围。宋刚肩挎竹篮站在一棵梧桐树下,微笑地看着每一个路过的人。有人注意到了他竹篮里的玉兰,看了看就走过去了。有一次,两个女孩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他的玉兰花,赞叹它们躺在绿叶当中真的很美很可爱。机会来了,宋刚依然只是微笑地看着两个女孩。他们走后,宋刚后悔了,觉得刚才应该多叫卖几声。那两个女孩可能不知道他在卖木兰花。
这时一个卖玉兰花的农村小姑娘走了过来,左手提着一个竹篮,右手拿着一束玉兰花,边走边喊:
“卖玉兰花!”
宋刚左手挎着竹篮跟在小女孩后面,右手还拎着一束玉兰。前面的小姑娘喊着“卖玉兰花”,后面的宋刚会害羞地说:
“我也是。”
一个农村姑娘看见一个年轻姑娘来了,立刻迎上去喊:“姐姐,买一束玉兰花。”
宋钢也跟他打招呼。他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说:“我也是。”
宋刚跟着这个农村小姑娘走出半条街,后面跟着说了不下十遍“我也是”。小女孩不高兴了,她回头生气地对宋刚说:
“不要跟着我。”
宋刚停下脚步,茫然地看着小女孩。这时,王冰棍手里捂着肚子走了过来,笑道:王冰棍在街上闲逛了一天。他看着宋刚手里拿着一束玉兰,不知道怎么卖,只知道跟着小姑娘说“我也是”。冰棒王笑得肚子都疼了。他上来给宋刚看,他说:
“你不能跟着人家屁股走……”
“为什么不能跟在后面?”宋刚说。
“我是卖冰棍出身的,”王冰棍自豪地说。“你跟在后面。如果人们买了前面的,谁会买后面的呢?就像钓鱼一样。不能两个人站在一起钓鱼,要分开。”
宋刚明确地点了点头,右手牵着木兰花,左手提着竹篮向小女孩的反方向走去。王棒冰又想起了什么,给宋刚打电话:
“人家小姑娘见了女孩子就叫‘姐姐’。你不能这么叫她。你得叫她‘姐姐’。”

宋刚犹豫了一下,说:“我说不出来。”
“那就别叫了,”王冰棍擦着嘴角的口水说。“反正你不能叫人家姑娘‘姐姐’。你已经三十多岁了。”
宋刚谦虚地点点头,正要转身走,这时王棒冰又叫住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钱递给宋刚,说道:
“我买两根弦。”
宋刚从王冰棍手里接过钱,递过去两串玉兰花,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