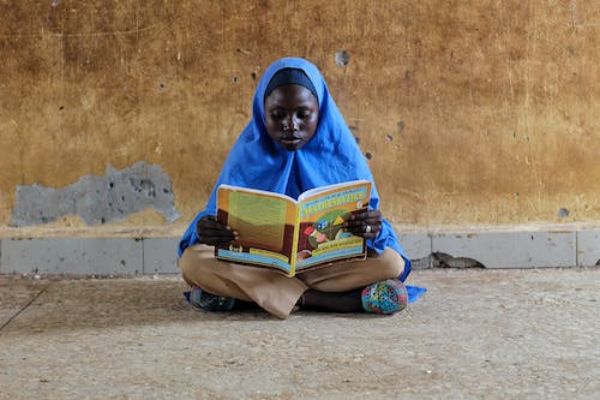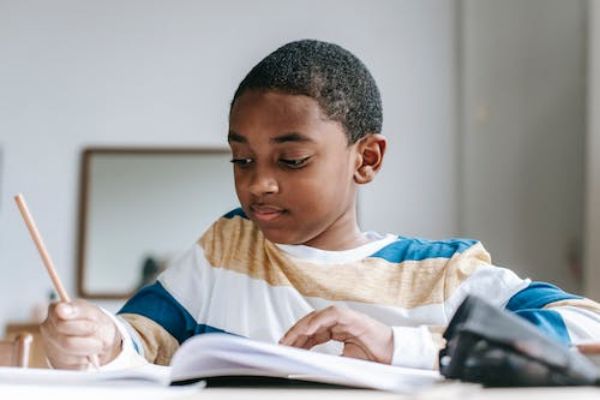苗寨,即苗族的人居住的村寨。苗族的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有关于五千多年前苗族先民的记载, 苗族的先祖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代活跃于中原地区的蚩尤部落(蚩尤和炎帝、黄帝一同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即中华三祖)。
西江苗寨位于 贵州凯里的东南,从雷山路口折向东北,位于雷公山东北面 ,距州府凯里39公里。是全国最大的苗寨,有5600多人,1250多户。所以称为千户苗寨。西江,是苗语鸡讲的音译,意思是苗族西氏支系居住的地方。世居者均为苗族,自称嘎闹。西江苗寨位于雷山东北36千米处。这里居住的是苗族西氏支系。千户苗寨四面环山,重峦叠嶂,梯田依山顺势直连云天,白水河穿寨而过,将西江苗寨一分为二。

西江苗寨,全寨苗族占99%。黎平肇兴侗寨有900多户 西江苗寨人家、3800余人,故有侗乡第一寨之称。全寨有5个家族,每个家族有一座鼓楼,共5座鼓楼、5座花桥、5座侗戏楼,这些极富侗族建筑特点的建筑物至今保存完好。
在西江苗寨可以享用苗家风味特色晚餐,席间接受苗家少女飞歌敬酒,在苗家吊角楼美人靠(凉台栏杆,苗家称为美人靠)上观千户苗寨万家灯火。还可以观赏铜鼓芦笙表演,晚上可宿苗家吊脚楼。
苗疆在哪它的历史是什么?拜托各位了 3Q
记得,跟友人闲聊时,说起“苗疆”在哪儿的话题。一友人脱口而出道:“就是苗族聚居地吧。”我于是追问:“苗族聚居地在哪儿?”哑火。
可以肯定的是,就算武侠小说里形容的“苗疆”,确指某个或某些地方,也不能跟“苗族聚居地”画等号。
而且,仅就“苗族聚居地”而言,今天跟共和国成立以前,也是有所不同的;更别说对比武侠小说幻化的“古代”了。
不同源自两方面:
第一是根本性的——苗族的定义,也就是苗族指什么、指谁?指向或说定义不同,聚居地也自然就不同了。
第二是地域性的——无论怎样定义,苗族作为一个民族,其所定居、聚居的地域,在历史上也是有调整和改变的。及至今天,苗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在“少数民族”当中,属于“多地聚居”的“较大者”。即:苗族从人口来讲,属于比较“大”的少数民族,且聚居地并不似其他“大小”可比的少数民族那样相对集中。
今天来说,苗族在湖南、贵州、四川都有聚居地,甚至在云南、湖北的一些地方,也有苗族。他们在本民族内部,有着不同的、或许牵连紧密也或许牵连不怎么紧密的分支,彼此的聚居地并不都“接壤”,甚至有的还相距遥远。

很显然,这些未必接壤甚至可能相距遥远的区域,不能套概念地被认作是“苗疆”。
说“苗疆”,先得说“苗”。
如同上面讲的苗疆不能跟苗族聚居地画等号一样,“苗”作为对种群的称谓,其含义,也不同于今天说的“苗族”。
我国古代,尤其上古至中古(夏商至隋唐),中心政权直接管理的区域大小不一,但一般都以“中原”和“关中”为核心。所谓中原,往大里说,概指以今河南省及周边的河北中部南部、安徽西部北部、山东中西部、湖北长江汉江以北地区,往小里说,就指河南省大部(南部除外);而所谓“关中”,指的是对应“中原”的“河西”部分,即今陕西省秦岭以北、黄土高原以南的平原、类平原区域。
由“中原”、“关中”构成的中心地带以外,不同朝代、同一朝代不同时期,管理模式不同,但对相对边缘的当时的少数民族(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汉化”、融合,今天已属汉族),却有着相对“稳定”的防备和带有轻蔑、歧视色彩的称谓。
上古时期(商周)在称谓上,是说“东夷、西翟、南蛮、北胡”。即中心地带以东(多涉及沿海地区)称“夷”;以西称“翟”(又作“狄”或“戎”);以南称“蛮”或“苗”;以北称“胡”。其中北、西两个方向上,称谓常混用,而对于南面,叫法相对固定;东南地区,因处在“夷”和“蛮”交界,也称“蛮夷”。
有说法称,“蛮”和“苗”,在古字里“相通”,在称谓族群时可互为替代。要是这说法靠谱,那就可以认为,“苗”和“蛮”相近,是对中心地带(称“中原”、“中国”)以南的少数族群的通称。如果把这个定义之下的“苗人”作为祖先,衍变至今,应该囊括了包括汉族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南、东南、西南的民族。
在由上古到中古的过渡阶段(两汉、魏晋),中原集权衰落,加上北方游牧民族轮番“入主中原”(五胡乱华)、汉族南迁(南朝)等多重原因,中原文化向南传播,很多曾经的“化外之地”,逐渐与南迁的汉族融合、共生;也有些汲取了中原文化,自我强大;广大的南方区域,出现了新的族群分化,开始有了相对“教化”的“苗”、“冥顽不化”的“苗蛮”、“百夷”、“百越”。地域上,“苗”更多是在汉族统治区域边缘相对平坦、富足地方;“苗蛮”则主要生活在相同或相近区域中崇山峻岭、艰险贫瘠之地;“百夷”主要指今云南省靠近贵州四川的部分和广西临云南部分;“百越”则指今“两广”大部和闽南地区。
中古繁盛期(唐宋),是“粟作文明”向“稻作文明”的转型期,中心政权的管理范围扩大,人文影响深远,曾经跟汉族“共生”的“教化的苗”,几乎完全融入;而同时,曾经的“苗蛮”,则迫于生存压力,或“向心”地靠拢被汉族“同化”的本族,或与“百夷”、“百越”竞争、共生,形成今天西南中南少数民族集群的前身。

相比较而言,这样的“苗蛮”,还是比更“化外”的“百越”、“百夷”们,多受了些中原文化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有限的)先进性,故而在竞争中显示强势,在共生中占据主流。武侠小说所主要涉及的年代,大约最早始于这个阶段。
随着历史发展,到近古(元明清),聚居于交通阻隔严重地域的“苗蛮”,又分化成诸多族群;其中一部分,是今天苗族的前身,也有相当一部分形成了另外的民族。提到“苗疆”的武侠小说所涉及的年代,通常比较晚的,便指向这个时期。
苗族在哪里
苗疆是指的中国西南部的地方,包括云南、四川、贵州、湖南、重庆等各省市部分 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苗疆全图,把沅江以西,酉江以南,辰江以北,及湘黔交界以东区域定为苗疆,东、南、北三面环水,西面以高山为屏蔽,横跨湘黔两省的大腊耳山逶迤而来,在其腹地因地质断层而构成台地地形,星星点点的苗寨散布于台地之上,凤凰城正在其间。城池被苗寨团团围住,双边的关系又相当紧张,这小城四面受敌的气氛一定令人不堪,断不会有今天这份和谐与悠闲。 对苗族祖先起源,众说纷纭。《战国策·魏策》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明清以来多以古代之“三苗”附会为后世的苗族,传说是以尚武强盛一时的蚩尤后裔,属于号称“九黎”的部落。在长年与炎黄尧舜禹各部落的争战中,多次战败,逐渐从其生息之地黄河下游与长江中下游被迫南迁,陆续定居于西南荒凉的崇山峻岭,史称“南蛮”,其中居住在湘鄂川黔地区的一部分,在汉唐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 湘西苗族流传的史诗《休巴休玛》,记录了苗族先民不断迁徙的历史。当他们还定居在“占楚占菩”(楚国江汉江淮流域)的年代,“繁衍如鱼如虾,收获堆积如山;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坚;生活越来越好,树屋盖瓦砌砖;女的戴银戴金,男的穿绸穿缎;牛马满坡满岭,猪羊满栏满圈”。后来遭到恶鬼“枷嘎”“枷狞”的破坏,被迫离开富饶的平原,迁往“高戎霸凑”(武陵山区边缘地带),在泸溪峒重新建设新的家园,“男的又来立家立业,女的又来积麻纺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炊烟绕过九十九岭,歌声响彻万里长天”,不料恶鬼追赶而来,“祸害遍及九十九岭,世上人间住不成家”。苗族七宗七房反抗失败,只得像“河里的鱼逆水而上”,从大河边被赶到小河边,从小河边被赶到小溪边。一次又一次的创业,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向更贫瘠的地区迁徙。如今已经很难想象苗族的先人当年是如何扶老携幼,恋恋不舍告别昔日的家园,一步步深入猛兽出入无常林深不见天日的湘西腹地的。苗人爱唱山歌,但即使是在今天的一些十分欢愉的场合,苗歌出口仍然会让人听来凄凉哀伤,那些哽哽咽咽断断续续的曲调,绝无半点娱人娱己的意思,反倒露出一步一喘气五步一回头的印迹,也许这些苗歌诞生的环境,正是苗家先人艰难险阻前途莫测的旅程吧。 到了明末清初,中原汉族人口激增,为解决人口与土地矛盾,不断侵占苗疆,而苗人已经退无可退守无可守,致使汉苗两族为争夺生存空间时时兵戎相见。苗族被一步步逼入西南山区的高寒地带,生存环境更趋恶劣。据《苗防备览风俗考》:“苗中四时气候与内地向异。常有黑雾弥漫,卓午始稍开朗。当朦翳之时,人畜对面不相见,寸趾难移。春夏*雨连绵,兼旬累月,常驻泥滓难行。雨势甫霁,蒸湿之气,侵入肌骨。其泉为山洞岩浆,性极寒冽,饮之败胃,水土恶劣,外人居其间,常生疠疫。”
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湖北、海南、广西等省。苗族有自己的语言,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瑫语族苗语支,分湘西、黔东和川黔滇三大方言。苗族聚居的苗岭山脉和武陵山脉气候温和,山环水绕,大小田坝点缀其间。出产水稻、玉米、谷子、小麦、棉花、烤烟、油菜、油桐等。2011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国内苗族人口达到1000万,在国外的苗族有约二三百万左右。从苗族的分布情况看,其特点是大散居,小聚居。从人数上看,聚居的人多,散居的人少。贵州省分布最多,遍布全省各地,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最多,也最集中,其余分布在毕节地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顺地区、铜仁地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六盘水市、贵阳市、遵义地区。